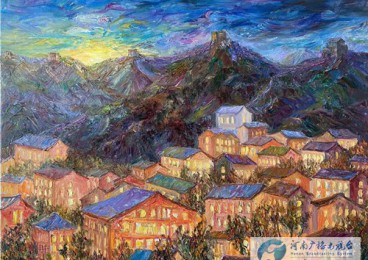作 者 : 王 欣
一
初到禹州,秋风便吹过我的胸膛,吹醒了我脑海中的一条小爬虫,我看见,它爬过西域的黄沙,爬上过边塞的落日;它爬过汉唐的芙蓉,又顺着老城墙,爬上城楼的皓月上了一棵老树。忽然,它又爬上云头,追着布谷的一路啼鸣,来到中原腹地。未曾想,这小小的爬虫竟然要带我追溯一段时代的风,走近穿越之旅。我细想了半天,这只爬虫原来是只馋虫,喜欢过甘肃定西的土豆粉、看过山西岚县的土豆花海,它迷恋过汉唐的石灰高墙,竟顺着意识的灵力,一直随我到了禹州的“器美、食美”的禹粉之乡。

“洗薯、打浆、蒸粉、晒粉,百年工艺,回味悠长,老祖宗的味道,就是地道”,脑海中的广告词萦绕着,仿佛是另一个我,在不停地完成意念的驱使,让我的行程和背包里填塞进“新农人、大工匠”的主题,即便抛开传承、融合、领跑、跨越的使命,我也无法拒绝;更令我无法拒绝的是从小爱好粉条的我,宽的、扁的,圆的各式形状都爱;土豆、红薯、芋头等各式材质亦都喜欢。更难以拒绝的理由是,我从小在泥土地里打滚,一望无际的田野安放着我的魂。一直很安逸。原本只想轻叩一扇窗,主人却为我打开了“穿越之门”:“农耕文明、农具缩影、农人粮心、工匠精神”等诸多的标签在我脑海快闪,倚着门框,在门环上侧耳,我仿佛听见百年前的叩门声,循着声音望去,我看到辛勤劳作的祖辈三五成群地散落在地里,像沉默的绵羊,只用洁白回馈蓝天。汗水掉进眼窝里,他们正拿衣襟擦拭;我还能看见田野上不知名的花儿摇摆在风中,我还看见几头悠闲的黄牛,正沿着河坝吃草;哦,我这个此刻叩门待进的人,在思绪的浅层偶作停留.......时光的河道里,我仿佛是跟随叩门的人一起再度踏入了流年。
二
红薯地里忙碌播种的场景如画,投掷在彩色屏幕上的人,他说:“他要将老祖宗留下的味道传承下去。”“守得住根,才能不忘记魂。”我亦在心中念叨。他的笑脸令我心旌摇曳,偌大的展览馆里,为何我能一次次梦回家乡,身处田园,闻着泥香,拥抱自然与纯真?或许答案的显现只是概念化的一种呈现。
当原先味蕾的触动随着意念的流淌,目之所及、由心感叹,普通人的平凡,在日常细节中精耕细作的投入与用心。在禹粉文化博物馆里看到数百年的制粉历史,看到了挖掘出的孙膑行军打仗为携带方便,把豆类和杂粮加工成了粉条,成了粉条的发明人;看到小粉条,大产业,小红薯,大市场定位下粉条、粉皮、焖子、鲜粉,发展的红薯制品、蔬菜制品、五谷特产、小菜系列、养生系列、豆制品近百种产品,我坦白,我欣喜。口腹之欲与美食的诱惑,令我想到的是千千万万的农人,头顶太阳面朝黄土,想到我们的父辈在春种秋收的守望里对土地寄予厚望,土地都回馈以更多的果实。而在传统的耕作之余,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多元化发展、农业文旅特色持续化、农业博物馆等背后的故事,或许才是令更多人思考和探究的全部。
三
禹州人自古就有种植红薯、制作粉条的传统,粉条作为禹州的传统名特产品,在全国劳动模范、禹粉大工匠——孙继周先生的带领下,与父老乡亲一起,将这项传统工艺传承并呵心守护,守望着千百年来农人守望的朴质,并将家乡父老在农田地里挥汗的过程、借力的家伙什、在红薯制作工坊里将细节与步骤推演;将祖辈传下来的技艺精磨深耕,将一块红薯作为土地上的宝贝疙瘩,不仅从产品历史和产品知名度上深究,还在生产工艺上、口感与形状上逐一打磨,让禹州薯粉成了继钧瓷之后的又一张特色名片。

盛田禹粉的保鲜技术,打破了传统粉条不添加明矾、做不成粉条的规则,而且实现了传统干粉条向方便即食鲜粉条转变的革命性创新。厂区聘请5位博士组成研发的团队,经常与农人、匠人吃住在一起。走过一扇门,听人说:“穿过这道门,你好似能从这儿穿越到任何一个时代。”意念的花苞还未打开,我就看到了“百年粉坊”“中华老字号”,粉粉可口益智平肝嫩容颜,薯薯开胃补虚健脾强肾阴。”顿时又让我陷入对这位劳动模范匠心精神的点滴过往中,感怀不已。
四
一根粉里有药王孙思邈,以薯养人的传承,据说有600余年的历史。禹州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是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夏朝都城、韩国都城、秦汉颍川郡治、金元明清的州府治所,钧瓷唯一产地、明清全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禹州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境内有具茨山文化、伏羲文化、黄帝文化、大禹文化、钧瓷文化、中医药文化等古文化;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孕育出韩非、吕不韦、张良、吴道子、晁错、褚遂良、郭嘉、司马徽等历史名人。华夏文明的火种,历史亘古不断,交叠传承,继往开来的道路上,一直有引领者,有追随者,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者。我想还会涌现更多的人、守护人,开创者一直都在路上。前赴后继啊,生生不息.....
“纸短情长”落在笔端,禹州纸面上的历史很长,阳翟是中国古代地名,位于河南禹州,为《史记》记载中夏启的都城,据传夏启曾经在此会盟诸侯进行钧台之享,曾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都城。夏朝时禹境称“夏邑”或“夏国”,亦称“虞国”《水经注》载:“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竹书纪年》载:“夏禹之子夏启,即位夏邑,大享诸侯于钧台,诸侯从之”。
不由想起丁进兴老师那句:“颍河里的诗经,在我的经络里穿梭、归来,少年坐在露珠上”,我就仿佛化作了颍河的水里一株水草,周身被阳光照彻,而根部所系的堤坝,牛羊成群走过,袅袅炊烟抬高天空,我就能坐在月亮上把白天的灰尘,一一抖落。
我承认我词穷了,在这么历史遗迹和名人滋养过我的的土壤上,所有时代的闪光一起向我探照,我朝着这块土地致敬,我颔首,感受到的是时代车轮下的凝重和庄严,一种历史的肃穆感从头顶一下子传输到脚底,我僵立在百年之门的跨越中,不断深思。让孩子门听虫鸣鸟叫,吃到原汁原味,撒着欢与自然拥抱.......书写和挥洒感受,生命打开通道,与时空链接,风不断吹过原野,有人接过古人的斗笠、改进祖辈的农具;有人经手停留,躬身其中,有人用心守望,在每一寸肌肤上,触摸春天花开,触摸秋天结果。而我能做什么?若以这飘渺微小的文字作为对游子的呼唤,会不会被人轻笑?可我脑海中的小爬虫异常激跃:放心吧,进家门若春风的献词未到,一定有老乡亲拙朴的微笑,他们会替我拍去一路风尘,迎接每个回家的孩子。
作者:王欣,笔名(水云魅影/ 若水飘) 别称,小九,籍贯,甘肃武威,现居河南郑州。纯心写字,见心见人见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