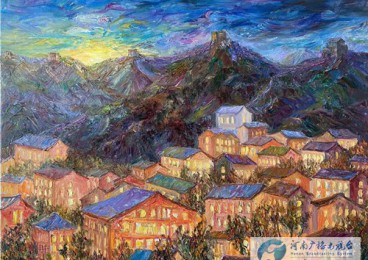七
1921年5月,8人取经队伍从上海出发,乘船经过日本长崎后又启程北上,三日后抵达海参崴。据确切情报,由日本武装支持的白匪帮,正在海参崴方面蠢蠢欲动,有包围和袭击海参崴的动向。王一飞决定:全体立即北上到伯力。否则,战斗一旦打响,就有出不去的危险。
曹靖华一行在紧张的气氛中离开了海参崴。不久,便进入了“真空地带”伯力。这里,各要口均为日本武装把守。火车到此也不走了。曹靖华他们不敢下车,只有躲在火车上,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个和他们在海参崴一起上车的红胡子(惯匪)头目,向他们这群小青年逼了过来。
“各位先生,火车到此不走了,下车到那边农舍里过夜吧,那里可舒服了。来,我帮你们拿东西。”红胡子边说边动手拿他们的东西。他把他们当成了富商,产生了歹心。
“谢谢你了,我们不去,就呆在车上。”曹靖华一边说,一边牢牢拉住红胡子拿到手里的东西不放。
红胡子把曹靖华打量了一遍,看到面前的这个青年人个子虽不高,但粗壮结实,特别有把手力,不好对付。
“好吧,你不要不识好坏。”红胡子凶相毕露:“不下车,把你们的金银珠宝都留下没事。”红胡子准备动武了。
“请你不要无理。”曹靖华浑身的青筋都暴了起来。一场可怕的搏斗眼看就要爆发了,他准备和红胡子进行战斗。空气紧张极了,其他的同志也都一起站了起来,做好了不测的准备。
正在这时,一列火车从北边风驰电掣地开了过来。曹靖华他们这时如鱼得水,未等列车停稳,他们一起飞跃而上,跳到了尚未停稳的火车上。但红胡子也跟着扑了过来。
“你们这群奸商,别高兴的太早了。”红胡子说:“这列火车到此也不走了,你们老老实实地跟我下车吧!否则老子就要动家伙了。”
“你不能这样无理,你不能抢我们的东西!”曹靖华他们和红胡子吵了起来。
这下惊动了列车工作人员。一个人走过来板着面孔,把曹靖华他们叫进了车务室严格盘查、威胁。
曹靖华想:“糟了,又是一群白匪帮,怎么办?”
“你们是干什么的?”高个子列车员问。他没有佩戴任何标志。
“新闻记者。”曹靖华说,并且拿出了“新闻记者证”让他看。
“到了海参崴,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列车员更加声色俱厉。
“我们想到前面去采访。”
“放老实点,现在搜查!”列车员不由分说动手搜查。
“你们不能随便搜查”。曹靖华极力反抗。
“好呀,抗拒搜查,是一伙日本间谍,推下车统统地杀掉。”
突然一片寂静。列车员在一个同志身上搜到了“秘密通行证”,他在细细审视。
“完了,这下全完了。”曹靖华想:“密件被搜出来了,没二话可说了。车外就是葬身之地,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啊!”
“哈哈哈哈.....”高个子列车员突然大笑起来,猛地伸出双臂,把曹靖华抱在怀里。曹靖华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弄得目瞪口呆,一脸惊愕,不知所措。
“我们是苏联红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咱们都是同志!”列车员发出一片欢呼,并急忙把藏在衣袋的红军符号拿出来给他们看。寂静的原野被欢乐冲破了,车厢里外响起了雄壮的国际歌声。
曹靖华等人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在1921年夏、秋,渔阳里6号先后有20多名学员分三批去苏联取经,被编为一个班。这些在建党前去苏联取经的革命先行者,以后大多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战线等方面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中坚力量。
八
从此,曹靖华与苏联、与革命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从此,苏联的马列主义源源不断地传入了卢氏山区。
在莫斯科,曹靖华紧握着他的苏联老师翻译瞿秋白的手,感到热血沸腾。因为瞿秋白的手曾紧握过列宁的手。书香门第出身的瞿秋白,学习过英文、俄文,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后,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8月,瞿秋白被《晨报》和《时事新报》聘为特约记者,前往莫斯科交流社会主义思想,次年见到列宁,听过他的演讲,面对面握手交谈过。瞿秋白是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的,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共访问莫斯科,瞿秋白是专门的贴身翻译。瞿秋白在中共党内地位和威望颇高,是我党早期的领袖之一。在瞿秋白的引导下,曹靖华走上了把苏俄进步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盗火的普鲁米修斯”道路。曹老的大作曾描写了在莫斯科与瞿秋白交往的情景:
“秋白,那是1922年吧,我们在莫斯科,你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你的一叶肺已经烂了,说你顶多能支持三两年。但你总不肯休息。讲课时,有时累的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了,但你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后来真的不能支持了,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高山疗养院疗养。我同韦素园几乎每星期日都去看你,你从来总是兴奋的忘了病,忘了一切。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有一次,在高山疗养院的病房里,针对当时曹靖华和韦素园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即一部分同学认为到苏联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指挥,立志当一名政治家或军事家,回国领导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才是唯一积极、革命的选择。而把精力用在学习俄语和关注苏俄文学上,便是消极的,逃避革命的表现。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狭隘、片面的看法。他说:革命是一条总的战线,它既包括着政治、军事战线,也包括着经济、思想、文化等等战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缺一不可。说着,他让曹靖华把病榻边小桌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递给他。瞿秋白几次面见过列宁,中国人面见过列宁的几乎凤毛麟角。瞿秋白从目录查到要找文章的页码,把书翻开,说:“你们听听,列宁在1905年写的《党组织与党的文学》这篇文章里是怎么说的。”接着念起来,并说:“列宁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同志和苏联共产党极其重视文学事业,把每一部成功的作品和军事上一次重大胜利或经济上的一次重大成功看得同等重要。所以,怎么能把政治、军事同经济、文化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呢?”瞿秋白循循善诱,拨开了曹靖华和韦素园心中的谜团,他们感到心里亮堂多了。看着曹靖华和韦素园的神情由凝重变得开朗,瞿秋白也高兴地笑起来。他问:“你们读过高尔基的《母亲》吗?高尔基1907年发表这部作品的时候,恰恰是1905年革命失败,革命由高潮落入低潮,人们情绪低落。孟什维克则高喊,‘没有必要拿起武器’。而高尔基却在《母亲》中通过巴维尔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的斗争事迹,告诉人们:‘真理是用血海淹没不了的!’工人阶级绝不能放下武器!”他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就接着说:“这部小说,擦亮了人们的眼睛,鼓舞了人们的信心,使他们重新集合起队伍向敌人进行斗争---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你们说,该如何估量高尔基这部小说的价值呢?”曹靖华和韦素园静静地听着、思考着。这些话,就像甘泉,一滴一滴渗入他们的心田。
九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曹靖华被瞿秋白伴着钢琴吟唱的《国际歌》声强烈地震撼了。这是从1923年春北平(解放后改为北京)东城黄化门瞿秋白的房间里飘出来的歌声。由于曹靖华在莫斯科患肺气肿,经组织批准,于1922年深秋回国,到卢氏山区养病。年底,接韦素园来信,到北京大学俄语系旁听,并旁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认识了鲁迅。1923年,瞿秋白受陈独秀邀请,回国工作,翻译苏共的一些著作,并在《新青年》等主流报刊上,撰写介绍共产国际、列宁等方面的文章。瞿秋白住在北平东城黄化门西妞妞房他本家叔叔瞿菊农家里。曹靖华下了课,经常去看他。瞿秋白住的是一个跨院,有两间小房,外间靠门的隔断前,放着一架小风琴。瞿秋白正翻译《国际歌》。他每译完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自弹自唱,仔细斟酌每一句歌词能不能恰当地配合曲谱。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译文,但瞿秋白都不满意。他希望不仅把词意译出,而且能唱,能流传。在翻译“国际”一词时,就颇费斟酌。因为西欧其他文字大都是同音的“英特纳雄耐尔”,而汉语意译的“国际”只有两个音节,唱起来效果不好。斟酌再三,瞿秋白决定用中文唱《国际歌》时,这一句用音译。这才有今天用气壮山河、排山倒海的气势高唱的“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浩气。这样不仅便于唱,而且由于各国字音相同,使中国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可以情感交融,同声相应。
1923年,在北平的瞿秋白,把曹靖华翻译的契诃夫剧本《蠢货》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并鼓励说:“中国文艺土壤太贫瘠了,你来做一个引水浇田的农夫吧。”瞿秋白要曹靖华做“引水”浇田的农夫,以笔代锄,辛勤耕耘,把十月革命的“水”引向中国的田园。
十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1925年的春天,曹靖华被开封行宫角临街的一幢二层小楼里飘出来的《国际歌》给吸引住了。虽然听得出是外国人用生硬的汉语唱的,但音调准确,旋律高亢。那幢二层小楼是苏联顾问团的驻地。曹靖华在《自述》中写道:“北伐实际上1925年就开始了。当时大致可分为三个据点:一是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是开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最初胡景翼在那里主持工作,为河南督办;三是包头的冯玉祥,是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国际向每个据点都派出了苏联顾问团。我在北大旁听,与韦素园一道受李大钊同志指派,于1925年春到开封担任顾问团的俄文翻译.....”唱歌的是苏联顾问团成员瓦西里耶夫,中文名字叫王希礼,被曹靖华小两岁,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班,来到开封国民军二军顾问团工作。曹靖华向瓦西里耶夫热情宣传中国新文化,推动瓦西里耶夫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为了解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他多次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为此给曹靖华回信四封,从此也开始了曹靖华与鲁迅长期的书信交往。王希礼翻译的《阿Q正传》是最早的俄译本,是我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先声,它改变了外国人只了解中国旧文化的局面,使鲁迅获得了世界地位和国际声誉。为传播中国新文化,曹靖华做出了贡献。
1925年夏天,在鲁迅倡议下,韦素园、曹靖华等人创办了进步文艺团体“未名社”,把翻译介绍苏俄进步文艺引为己任,自费印刷译著和编辑期刊。同年8月,经瞿秋白推荐,曹靖华的译作契诃夫名剧《三姊妹》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曹靖华决心像瞿秋白告诫与鼓励的那样,不辞劳苦地、把苏俄进步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引水浇田的农夫”。
1926年1月,开封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失败。李大钊对回到北平的曹靖华说:“开封的情形,我们都知道了,你回来就好。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原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由于曹靖华在开封给顾问团做过翻译,有经验,所以李大钊决定指派他担任苏联顾问团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
1926年四、五月间,曹靖华赶到广州。离开北平时,古城沉浸在“三·一八”惨案后白色恐怖的萧瑟气氛之中。而革命策源地广州,却是阳光和煦、木棉盛开,处处洋溢着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气象。顾问团办公地点在广州的东山春园,即现在的新河浦路那三幢外形一样的洋房里。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北伐战争就此轰轰烈烈展开了。曹靖华跟着加伦将军(即苏联元帅布留赫尔),随北伐军总司令部前进。当时广州的火车只通到韶关。北伐军下车后徒步行军,翻过大庾岭到乐昌,改乘木船抵达株洲,再继续乘火车北上。北伐军汀泗桥激战取胜后,曹靖华随加伦将军乘火车一直到咸宁纸坊车站。紧接着,又乘胜攻克了贺胜桥,突破了吴佩孚在武汉的最后防线,总司令部于暮色苍茫中抵达南湖。
在一个大敞院里,曹靖华看见院墙上放着许多攻城的“云梯”,一个人站在院中的高台上,正向当夜攻城的战士们进行动员。走近一看,原来是郭沫若,他当时是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总政治部和总司令部两个部门,总是肩并肩随战局发展一起向前运动的。由于北伐军没有重武器,战斗很激烈,伤亡也大。那一夜攻城没有成功。总政治部顾问处的纪德甫同志也在攻城战斗中牺牲了。纪德甫同志是山东人,中学毕业后去苏联留学。他牺牲时,只有一只手表和一个旧钱包,里面只有两个铜板和两张当票。当时北伐军自广东出发直到武昌城下,未发过一次军饷。郭沫若在哀悼纪德甫同志的一首诗中写道:
一棺盖定壮图空,
身后萧然两板铜。
沉稳如君偏不碌,
人间何处吊英雄?
那时参加北伐的人中,荷包里只有两个铜板外加两张当票的,绝非纪德甫一人。是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城。
1927年1月1日,国共两党联合组成武汉革命政府。是年春,曹靖华跟着加伦将军随北伐军总司令部进军江西。一次行军中,加伦将军对曹靖华说:“曹同志,你不能留在这里了。你没有感觉到,蒋介石就要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动手了。你夫人和女儿都在武汉,你应当设法回武汉。”
曹靖华联想到不久前,蒋介石曾似有意无意对他说:“你刻苦勤奋,工作努力,跟着我好好干吧,将来一定前途无量。”曹靖华与蒋介石只是工作关系,尽管他对蒋介石与加伦将军讨论作战计划意见相左时,急躁、自负、动不动发脾气、骂人非常不满,但他从不介入,恪守着一个翻译人员的职责。此外,他与蒋介石并无私交。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对自己讲这些呢?当时只感到唐突。此刻他忽然顿悟:原来蒋介石是在动手之前笼络人心呢。
事不宜迟,曹靖华在加伦将军的安排下,请病假回到了武汉。曹靖华离开江西三天,蒋介石便开始清党,随之又策划了“四·一二”政变。1927年秋,在党的安排下,曹靖华冲破了反革命的刀光剑影,再赴苏联。
十一
“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在莫斯科“红场”激荡,瞿秋白和曹靖华向列宁墓三鞠躬。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瞿秋白在武汉组织召开“八·七会议”,28岁的他被选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政治局和常委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前往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便是在此次会议中决定的,并由瞿秋白安排的工作任务。1928年5月,瞿秋白同志再次来到莫斯科,以中共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常驻莫斯科。曹靖华1927年秋到苏联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俄国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与曹靖华一直以“老学长”相称的杨尚昆(杨尚昆1926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初回国,1988年4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及伍修权等,均是那一时期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工作之余,曹靖华去看望了老朋友加伦将军。不久,加伦将军离开了莫斯科,赴西伯利亚出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故友重逢,万感交集,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
浮光耀金的莫斯科河水,映照在瞿秋白瘦削而坚毅的脸上。瞿秋白和曹靖华沿列宁大街、红场、莫斯科河畔边走边谈:“靖华兄,中国革命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食粮。我们的革命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我们必须把失败了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向反动派重新发动冲锋。这就需要大量的苏联革命文学和文艺理论。你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瞿秋白和曹靖华谈话后,为便于翻译苏联文学,1928年秋,曹靖华到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及列宁格勒大学(现为圣彼得堡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曹靖华去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后,仍一直保持着与瞿秋白的联系。他还时常专程去莫斯科看望瞿秋白,见面总有谈不完的话题。1929年冬,曹靖华接到鲁迅先生约他翻译《铁流》的信,要他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他立即像瞿秋白同志要求的那样,把翻译《铁流》“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来完成”。1931年“五·一”节前夕,曹靖华完成了被冠以世界文学名著的长篇巨著《铁流》翻译任务。曹靖华把《铁流》的译文和其他的复写材料,整齐严实地封成两个包,然后用双挂号信,一包寄法国友人,一包寄比利时友人。再请这些朋友换上新的封皮寄给鲁迅。1932年,《铁流》中文译本在中国出版了。鲁迅先生给《铁流》写了编校后记。瞿秋白翻译了绥拉菲摩维奇的《我怎么写<铁流>的》,并给小说作了不少注解。《铁流》的出版,厄运多端。原出版商怕反动派杀头,撕毁了合同。鲁迅先生冒着极大的危险,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名称《三闲书屋》,自己拿了一千元大洋出版。所谓的“三闲”,是指鲁迅、曹靖华和瞿秋白三人。尽管《铁流》一出版,立即像《毁灭》等书一样,又遭到反动派的严禁。但鲁迅先生通过与他为莫逆之交的日本友人内三完造先生,在上海的内三书店柜台底下,一册一册地将初版一千册《铁流》,渗透到读者手中。《铁流》在中国影响深远,尤其对激励大批青年投身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长征途中,大家都抢看《铁流》,用《铁流》精神坚定革命信仰,鼓舞革命斗志,克服艰难险阻,完成艰苦卓绝的长征。
对于和瞿秋白的交往,曹靖华在回忆文章中记述到:“1929年,有一次,我从列宁格勒到了莫斯科。临走前,到你住的地方----留克斯饭店看你。你总是像从来那样昂奋,那样忘我地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打算。你谈笑风生、热情洋溢地谈起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谈得使我差点误了火车。是1929年深秋吧,你回国前,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在我家里畅叙半日。不意那次相会,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会见!”
瞿秋白同志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于福建省长汀县突围时被捕。蒋介石听到瞿秋白被抓住的消息,十分高兴,从南京派来专人劝降。但瞿秋白根本不是那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墙头草。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英雄就义,正值36岁壮年。赴刑场路上,瞿秋白高唱《国际歌》,并给了巧遇的乞讨少年一块银元,押解的国民党士兵为之动容。
按照蒋介石命令,执行处死瞿秋白的国民党军队师长宋希濂,早年在黄埔军校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特赦后在晚年对此事极度后悔,多次提起都泣不成声,说自己对不起“恩师”瞿秋白的教导。
瞿秋白牺牲后的纪念日,他的妻子杨之华常写文章悼念:“秋白同志,你最后的红军歌、国际歌声,使我们全体战士热血沸腾。你临死前的安宁,正是你已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亲眼看见了人民自己的政权。”
2019年深秋,笔者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徜徉。当我向列宁墓三鞠躬的刹那间,《国际歌》在我心中激荡,仿佛90年前瞿秋白和曹靖华向列宁墓三鞠躬的情景再现。在莫斯科留克斯饭店,我流连忘返:这是1929年曹靖华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看望瞿秋白下榻的地方。我还有幸与俄罗斯红旗歌舞团列宁的特型演员合影留念。在卢氏县,曹老拉住我的手,鼓励我大胆往前走。在莫斯科,列宁拉住瞿秋白的手,瞿秋白拉住曹靖华的手,向着革命的路,向着革命文学的路大胆往前走。我虽然拉的是列宁特型演员的手,但仿佛拉的是列宁的手。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我站在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塔旁,这里射向冬宫的炮声仿佛在耳边回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声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瞿秋白要曹靖华做“引水”浇田的农夫,以笔代锄,辛勤耕耘,把十月革命的“水”引向中国的田园。1929年深秋,瞿秋白要回国前,最后一次到了列宁格勒,在曹靖华家里畅叙半日。不意那次相会,竟成了他们最后一次会见!

白旭东2019年秋在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留影

白旭东2019年秋在莫斯科与红旗歌舞团列宁特型演员合影
白旭东2019年秋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留影。十月革命时,在圣彼得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炮轰冬宫。该舰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闻名于世。
十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第一次激荡在天安门广场!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的曹靖华,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是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的!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朱德总司令宣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举行宏大的群众游行和庄严的阅兵仪式。曹靖华陪同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法捷耶夫象根栽在地上的电线杆,浓眉高耸,目光炯炯有神。他就是苏联著名小说《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此时的法捷耶夫,虽然脱下了戎装和长筒皮靴,但仍不减雄赳赳军人气度和十月革命风暴中硝烟弥漫里游击战士的本色。在这庄严而神圣的时候,曹靖华的眼睛湿润了......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的。在周恩来提名下,曹靖华出席了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编为政协文艺界小组。该小组共有10人。按合影照片顺序,自左至右,前排:艾青、巴金、史东山、马思聪;后排: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会议完成了历史性的重任: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宪;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由北平改称的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还决定了国旗与国歌。
曹靖华站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一个个镜头飞快地闪现:1933年8月,他从苏联回到中国,化名张敬斋,隐蔽在北平的小汤山,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东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任教。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周恩来为名誉主席,曹靖华等45人为理事。1939年春,在周恩来提名下,曹靖华任改组后的中苏文化协会理事,担任《中苏文化》月刊的常务编委。之后,曹靖华还兼任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分管两套丛书--苏联文艺丛书和苏联社会科学丛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如今,面对天安门广场红旗的海洋和钢铁的阅兵方阵,曹靖华内心里经历着、体验着这最庄严、最神圣的时刻:祖国啊,人民啊!贫穷、愚弱过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感到幸福,同时感到身边的这位朋友--《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伟大作者的亲切。法捷耶夫以及他的作品与眼前已经诞生的新中国息息相关。曹靖华亲切而又无限感激地回答着法捷耶夫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的小说《毁灭》,蒙我最崇敬的世界伟大作家鲁迅先生亲笔翻译,我终身感到莫大荣幸!……”法捷耶夫一再谦虚地说。
“鲁迅先生在1930年底翻译您的《毁灭》,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他又不懂俄文,是从日文翻译的。”曹靖华接着说:“书翻译出来了,出版社不敢出。最后鲁迅先生自己拿钱,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刷出版。书出来了,又遭到反动派的严禁。鲁迅先生就通过日本友人内三完造先生,在上海内三书店柜台底下,一册一册地送到革命者手中......”
“唔!太令人感动了!” 法捷耶夫耸耸肩膀,以俄国人特有的习惯,表示感激说:“感激不尽,感激不尽,真应当好好谢谢他。”
“快别这样说,我们才应当感谢您呢!”曹靖华说。
法捷耶夫睁大着眼睛,带着疑惑的神态,望着曹靖华,催他快点说下去。
“我们是应当感谢您呢!真的,中国人民应当感谢您。”曹靖华恳切地说:“您写的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书,就是我国起义的奴隶们的军火、精神食粮,教育了中国人民,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我们今天的胜利,也有您一份功劳,中国革命感谢您......”
天安门广场上,浩浩荡荡游行队伍的欢呼声,阅兵式上给毛泽东主席乘坐的小车开路的“谢尔曼NO·237438W14”美国坦克车的轰鸣声,汇聚成时代的最强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注:曹靖华(1897年8月11日—1987年9月8日),河南省卢氏县人,中共党员,翻译家、散文作家。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系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1987年5月,获苏联列宁勒格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是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其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作者简介:
白旭东,男,1954年出生,河南省卢氏县横涧乡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历史学副研究员,卢氏县拔尖人才,三门峡市首届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1972年参军,1979年从警,1982年到县委办工作,1983年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科就读,1985年毕业回卢。1986年6月起,历任乡党委副书记、县委党史办主任、县委办副主任、县委办第一副主任等职,现为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1974年以来,发表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散文、小说等作品近百篇,先后出版历史专著4部200余万字。

白旭东,河南省卢氏县委党史办公室退休干部。退后,在西安市随儿子定居。夏天回卢氏县避暑。
邮编:710119 陝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紫薇田园都市D区19号楼4单元202室白旭东13939818176宅电029-88170567 QQ邮箱26940652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