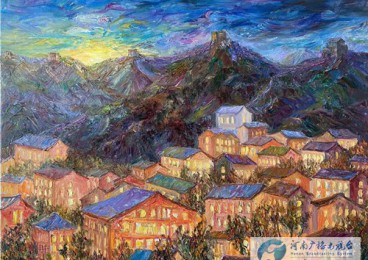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友人好心,在我办公室里用玻璃拼粘了一个鱼缸。配上几块上水石堆叠成假山,清澈的水漫上山头,点缀两样娇嫩的水草,室内现时有了景致,煞是养眼。
起初,友人让弄些金鱼来养,我想也是,这么有型的自制鱼缸,养些金鱼倒也增添情调。然而烦恼由此而生,不知是我懒,抑或工作忙的缘故,好好的金鱼在我的粗心照料下,总是熬不过月余。鱼缸中只剩下一池清水和堆砌得象假山一样的石头,一些水草掩映在其中,算是增添了些许的生气。每每看在眼里,心中不免惆怅。
此后,另有几友人到我办公室办事,看到空空如也的鱼缸,大笑。说我就是一浑人,这么大的鱼缸,也不养些鱼,岂不浪费,也显得我这个人没有品味。
我不禁哑然失笑,只以实情道出,非我不想让鱼在鱼缸中嬉戏,实为鱼宁死不愿在缸中屈就啊。平时在单位可以天天换换水,用容器舀水拨洒于石头上,看鱼缸中金色的鱼争相散去又聚来,倒也乐趣无穷,可若遇上节假日,三两天人不在,鱼就耐不住,接连离我而去。最让我难过是,清明节放假也就三天时间,当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是鱼缸内横七竖八的翻肚鱼,我数了数,整整十一尾,把我心痛的呀,两天都没精打采的。从此我便不打算在鱼缸中放金鱼了,把剩下的几尾也送给了同事。
友人听罢我的解释,纷纷给我出主意,劝我养一些好养活的东东。这不禁又勾起了我的兴趣,大家在一起商量半天,有让养螃蟹的,有让养小乌龟的,有让养泥鳅的,经再三斟酌,我决定养几条泥鳅,一友人自告奋勇说,一周内一把儿泥鳅到位。大家哈哈一笑,我也没当真。
哪知一周后,我从外面出差回来,打开办公室的门,端起茶杯悠然地走到鱼缸前看水草新发的嫩芽。有了鱼缸后,我已有一习惯,平时有空的时候总要看看鱼缸里的水草又发出嫩芽没有,金鱼养不活,水草倒还争气,慢慢的还长得像模像样,心里也有了一丝安慰。
猛然间,发现鱼缸底部泛起了水晕,真的是不仔细看还瞧它不见,在稍有浑浊的水缸底部的石缝间隙,几条清灰色的泥鳅轻微地摇着尾巴,一条头向外的泥鳅顶着长长的胡须,一动不动,像是提高了警惕,提防外面的侵扰。我兴致陡增,用一片草叶撩动清水,骚扰这些突如其来的不速客。心里不仅暗暗感谢友人的用心,友人一定是通过办公室要来我的钥匙,悄悄地把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放到我这空荡已久的鱼缸里的,想着一定要把这些泥鳅养好,给友人一个交待,也给自己一个说法。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美好的结果。那年国庆假期,恰逢二十年一遇的中秋国庆重逢。我兴致勃勃而去,因适前与友人曾探讨过泥鳅好养,在更换了新鲜的鱼缸水之后,便踏上了假期的旅程。
可归来上班的第一天,鱼缸里那几条被我当作宝贝的泥鳅,就生生的给我上了一课。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几个黑黢黢的像毛毛虫一样蜷曲的炭棒,着实地吓了我一跳。走近一看,是我鱼缸中的那几条泥鳅,严重的变形扭曲,已经风干了。地板上凡是泥鳅翻腾过的,都留下了淡淡的血迹。我急忙走向前去,用一支圆珠笔搅动鱼缸里的水,看看还有没有安分守已的存活下来的泥鳅,遗憾的是,一个不剩,我再数数地下的“标本”,确定无疑,全在!
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又是怎样的一种抗争啊!
短短的八天假期,一群我自认为生存适应能力极强的生灵,跳离我为它们准备的“温床”,为着生存而奔向死亡。看着地板上泛乌的极不规则的血迹,仿佛看到几条泥鳅为呼吸到新鲜氧气而逃离束缚的决然决绝,它们毫不畏惧,此起彼伏跳舞,场面是如此“壮观”,却无助得那样凄惨!
我的心隐隐作疼,泥鳅死了,害它们的是我!缺乏养泥鳅知识的我,与度娘进行了一次深谈。
度娘:泥鳅,小型底层鱼类,喜欢栖息于静水的底层,常出没于池塘、沟渠和水田底部富有植物碎屑的淤泥表层,对环境适应力强。
这没错呀,我给它们提供的环境不亚于它生活的环境呀,可它为什么一个个还是弃我而去了呢?
度娘:当天气闷热或池底淤泥、腐植质等物质腐烂,引起严重缺氧时,泥鳅也能跃出水面,或垂直上升到水面,用口直接吞入空气。
可能是我的鱼缸内缺氧造成的吧,我这样嗫嚅着。
但我还是不能释怀,假如我不作好事者来养它们;假如我不是一去七八天;假如它们跳出水缸时我正好在办公室;假如……
人就是这样,常常会叶公好龙,附庸风雅。
我真的很难过。我想真心待一件事,可又没有充足的精力和经验,我的粗心大意和粗枝大叶,往往又是我后悔的诱因。此时,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你不能给予什么,就不要苛求什么。对于金鱼也好,泥鳅也好,自然的环境里,它们可能生活的很好,对于特别有心的人可能养的很好,但于我,却是不相宜。
看着空荡荡的鱼缸和上水石上青葱的水草,我决心不再放养任何生物。但,我也不能懒惰,还要经常给鱼缸换水,为了每日陪伴我的充满生气的水草。
致,我那些已经远去的泥鳅!(本文作者:王朝阳 中共方城县委老干部局)